VR設備就算有小黃油產業做支撐,但是暈動癥的問題不解決的話這個市場也是沒戲,來看看為什么。

近年來,虛擬現實行業徹底火了。
各大企業紛紛推出VR設備,許多游戲被制作成VR版本,我們也能看到越來越多的行業在采用這一技術。
但在這場盛況背后,暈動癥這一根本問題仍未徹底解決。
事實上,傳統游戲的設計思路無法完全適用于VR,把熱門游戲改造成VR版本是再糟糕不過的做法。
這種生硬改造的做法需要推倒重來,我們需要完全摒棄傳統游戲,從零開始為VR設計一個全新的平臺,否則VR游戲永遠不會告別萌芽階段。
今年年初問世的VR版《輻射4》讓人有點小失望。
最近推出的Oculus Rift版《我的世界》帶來的同樣是失落。
平心而論,這款游戲很炫酷很有趣,向玩家展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游戲世界,但它經VR技術改造后效果很糟糕。
上世紀80年代,賽伯朋克(Cyberpunk)流派的科幻小說曾預言將來會出現“VR反烏托邦(VR dystopia)”式的糟糕境地,而如今我們已經很接近這種境地。
現在市面上出售著價格沒有貴到離譜的VR頭盔,硬件處理能力足以打造效果還不錯的虛擬世界。
而索尼、微軟、Facebook、谷歌等大公司正投入大量資金用以研發VR技術。
盡管如此,游戲設計師似乎總是停留在舊思路上,這幾年過去了,大多數設計師仍沒有展開相應的調整。
自游戲界對虛擬現實的首次嘗試之作Virtual Boy以來,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。
那就是,玩家在游戲世界里無法實現真正的移動。
在虛擬現實中,尤其在佩戴Oculus之類的頭盔時,玩家可以環顧四周,但不能四處走動,即真正地融入到游戲的虛擬空間中。
正因為如此,一些玩家跟隨角色在游戲空間中移動時,很快就會出現不適。
脫下頭盔后也會感到惡心或不舒服。這種體驗很糟糕。
而大多數設計師的回應是,讓游戲角色瞬間移動。《我的世界》就是這么處理的。
玩家可以讓自己通過空間轉換實現瞬間傳送。
對于這么重要的問題,采取這種不痛不癢的解決方案,效果肯定不理想。這讓VR鼓吹者所宣揚的諸多美好都幻滅了。
HTC Vive這樣的可提供房間規模VR體驗的頭盔效果也沒有好到哪里去。
房間規模VR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玩家在游戲中移動的問題,但仍然存在諸多局限。
《Space Pirate Trainer》充分理解了這些局限,并加以利用。
不過,這仍然無法徹底解決上述問題。
那么,究竟該怎么辦?
從零開始設計VR游戲。把熱門游戲改造成VR版本是再糟糕不過的做法。
數十年來,游戲的設計思路一直是,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在游戲空間中移動。
《超級馬里奧》、《鬼泣》和《輻射4》中的跑或跳等移動方式體現了傳統游戲的設計主線。
而從零開始設計VR游戲,意味著我們需摸索如何充分融合VR技術。
目前生硬改造傳統游戲的做法需要推倒重來,否則永遠無法擺脫這種別扭的游戲體驗。
目前看來,VR技術較適合戰略類和社交體驗類游戲。
《Ascension》、《Werewolves Within》等游戲并不打算挑戰VR技術的局限,而是試圖適應目前的技術水平,尋找最合適的平衡點。
這些游戲都專注于把玩家聚集在同一個虛擬空間中。
在社交體驗上,其他技術無法與VR相媲美。
這些游戲也充分證明了VR技術能夠開發出品質上乘的游戲作品。
《Space Pirate Trainer》是另一個不錯的例子。這個游戲采用了房間級VR,但玩起來如同VR版《Galaga》。
玩家在游戲中移動時不會感到拘束。如果游戲空間變大了,那么游戲體驗就變得很宏大。
《Chronos》也是個絕佳范例,它的格斗風格類似《暗黑血統》,而且沒有采用第一人稱的角度。
這款第三人稱游戲讓玩家感覺自己如同固定在墻上的蒼蠅,或者是一架看不見機身的相機,觀察著周邊發生的事件。
這讓玩家不必在游戲空間中尷尬地或不連貫地移動,從而避免了暈動癥。
戰略游戲也是個例外。設計者讓玩家如同神一樣,擁有無所不知的統管戰場的視角,因此VR發揮著一種自然過渡的效果。
即使是飛行模擬游戲,在玩了一小會后,玩家很容易就會感覺疲倦。
使用控制器來引導船舶或飛機讓人感覺很不暢快,總覺得缺少了控制桿。
但大多數玩家未必樂意買這種價格不便宜的硬件,而且每種游戲都配備一個控制桿也不大現實。
目前,VR的發展狀況有點類似早期的智能手機游戲或3D產品。
這項新興技術可用來制作各種酷炫的體驗,但我們需要擺脫舊思維。
傳統游戲的設計思路無法完全適用于VR,除非我們采用一些新工具。
其實,更可取的解決途徑是完全摒棄傳統游戲,從零開始為VR設計一個全新的平臺,否則VR游戲永遠不會告別萌芽階段。
另外,VR成人行業的發展較為迅速,吸引著大家的眼球,但“暈動癥”如果不解決,VR色情也沒戲。

 未來VR世界看房是這么看的
未來VR世界看房是這么看的 美國運用AR技術來管理城市
美國運用AR技術來管理城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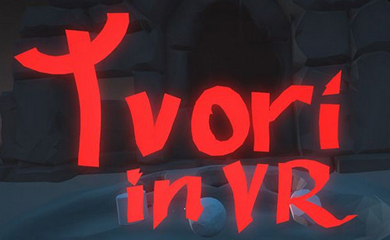 Tvori體驗版正式上線 VR動畫創作工具
Tvori體驗版正式上線 VR動畫創作工具 VR是怎么欺騙我們的大腦的
VR是怎么欺騙我們的大腦的 谷歌街景數據制作3D城市點云模型算法評估
谷歌街景數據制作3D城市點云模型算法評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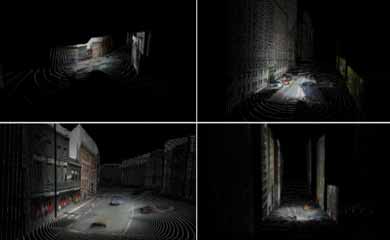 谷歌3D城市點云模型合成點云方法
谷歌3D城市點云模型合成點云方法

 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836號
湘公網安備 43011102000836號